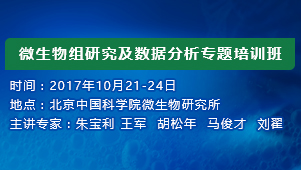他曾放弃科研10年,“不懂化学却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来源: 知识分子 发布者:张荐辕 日期:2016-03-18
编者按:
3月14日,应用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白茨格(Eric Betzig)应邀在北京大学做了两场公开演讲,这位在光学成像技术领域做出过多次重大突破,使得观察活体细胞内的生理过程成为可能,大大推动神经生物学研究进程的物理学博士,却被妻子、华裔物理学家吉娜戏称为“不懂化学却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白茨格回顾了自己在职业巅峰放弃科研,当过全职奶爸和汽车配件厂的机械工程师,差点与诺奖失之交臂的另类科学家生涯。他把自己的许多人生感悟诚恳地与中国的年轻科研工作者分享,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他说,自己做科研最重要的源动力,就是追随初心。要想有所发现,就要勇敢地走人迹罕至的小道,而非熙熙攘攘的大道。
作为一位诺奖得主,白茨格却认为“追求得奖对科研是有害的”。因为“科研成就是客观的,但是评奖是主观的,只代表某一个评奖委员会的观点,即便诺奖也是如此。如果你把得奖当成工作的动力,那么你的驱动力就是错误的。”
他说,科研工作者要爱护自己的声誉。“没有什么比你的声誉更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做好你的工作,你要诚实地工作,你要公平地对待别人,否则真的会有报应。你的声誉是你最重要的资产,要好好维护。”
他还用很长的篇幅回顾了他和多年的好友和同事、哈拉尔德•赫斯(Harald Hess)一路合作研制出光激活定位显微术(PALM)显微镜的故事。他们年轻的时候一起努力工作,相互激励,互补互学,中年时又互相帮助度过职业生涯的迷茫期。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都要感谢他。
“也许是看多了科幻小说,我一直都希望能做出一些东西,看似异想天开,结果拯救了世界。其他人都觉得是比较不现实的领域,正是我喜欢做的。”
3月14日,应用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白茨格(Eric Betzig)站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大讲堂,对台下座无虚席的年轻学子们这样说起鼓励自己走上科研之路的原动力。2014年,因为在超高分辨率荧光显微镜术(Super-resolution Fluorescence Microscopy)方面的贡献,诺奖委员会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白茨格与另外两位研究者Stefan Hell 和William E. Moerner,以表彰他们将光学显微镜由微米(µm,10-6米,百万分之一米)带入纳米(nm,10-9米,十亿分之一米)级尺度的贡献。
他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用自己多年来的亲身体验和科研成果,描述了自己不走寻常路,追随内心激情的人生历程,并介绍了自己对科学研究的深刻感悟。
“化学认识我,我不认识化学”,白茨格说,虽然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给他颁奖,但他实际不懂化学。他承认化学在大一过后都还给老师了。他是这样自我定义的:“我不是物理学家,不是化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我是工程师,光学工程师,为生物学家开发工具,帮助他们看到活体内的分子”。
白茨格身上的诺奖光环吸引了北大莘莘学子前来听他演讲。然而,白茨格却坦言“追求奖励本身对于科研是有害的”。他说,“尽管科研成就是客观的,但是评奖是主观的,只代表某一个评奖委员会的观点,即便诺奖也是如此。如果你把得奖当成工作的动力,那么你的驱动力就是错误的。你就应该去找点别的事情做。” 他的这番表述与国内科研界目前经常听到的所谓“诺奖级工作”和为名誉地位而工作的浮躁风气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还有些激动地说,“当我和赫斯(编者注:Harald Hess,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和同事)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单分子时,说,‘哇,我们做到了’。这才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刻。我的经历告诉我,最好忘掉诺奖,专心于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从物理学家到机械配件厂工程师
今年56岁的白茨格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他于1983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学士,并在1988年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工程物理学博士学位。
他在念研究生时便立志:要以“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即超高分辨率)观察生物活体成像,这在当时是天方夜谭,但他为此目标矢志不渝,奋斗至今。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白茨格就职于贝尔实验室半导体物理研究部门,继续他博士论文所开辟的研究方向,研制第一台超分辨率光学显微镜,叫做近场光学显微镜(Near-field Scanning Optical Microscope)。这种显微镜不仅大大提高了传统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而且首次实现在室温条件下观察并对单细胞分子进行成像,定位精度为12nm。一系列Science论文的发表为他奠定了近场光学显微技术(NSOM)领头人的地位。
在贝尔实验室,白茨格还与好友,从事低温显微镜技术的科学家哈拉尔德•赫斯(Harald Hess)共同进行着另一项开创性研究,尝试利用光谱照射进行细胞分子成像的研究。
尽管两个人是好朋友,但他和赫斯在一起共事的时候也常常彼此“较劲”,甚至是有些疯狂地工作着。在北大的讲台上,白茨格回忆,他每天早上4:30就会到实验室开始工作,如果发现赫斯的车先到停车场,“我会走过去,摸摸他的车看他的引擎盖有多热,这样就知道他比我早多少分钟到实验室。而他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两人一起从早上4:30工作到7:00,然后一起打网球,再一起工作到下午6点,然后晚上在同一家中餐馆吃饭,再继续工作至晚上10点。他说,“一个礼拜七天,天天如此。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五年。”
然而,随着科研的进展,白茨格却发现近场光学显微技术存在技术瓶颈,另一方面随着自己论文的发表,这项技术得以普及,更多的科学家加入进来,让这一领域变得不再“曲高和寡”,这也让热衷于从事开创性工作的他感到倦怠。
白茨格打了一个比方,做科研就好比养育孩子,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你希望他能当总统,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你对他的期望值越来越低,也许最后就是“只要不进监狱就好”。
他回忆说,“对我来说,做科研最幸福的时候,就是你在尝试,失败,再尝试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终于有所发现。一旦你发了论文,其他人了解到你的这项技术,人们会吹捧这项技术,把它捧上天,而实际上,作为发明者却看到技术自身的局限性,这让我感到沮丧。感觉过去12年我的工作纯粹是浪费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
在意识到不可能将光学显微技术的分辨能力推至纳米极限后,1994年,白茨格意兴阑珊,决定离开学术界,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在当了一段时间的全职父亲之后,他加入了父亲拥有的安娜堡机械公司,参与研发工作。在这里,他开发了一种生产汽车配件所需的自适应液压伺服技术(FAST)设备,但并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白茨格说,“我耗费四年发明这种设备,又花了三年尝试把它卖出去,结果只卖出两台。”这让他意识到,或许自己不很擅长做一个学术科学家,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无缘做一个精明的商人。“在花掉我父亲100万美元和自己七年的时间之后,我不得不告诉父亲,这个我做不了。”那是2003年,白茨格不仅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 “那真是我人生中最惨淡的一段时光”,他说。
在大自然中找回初心
这时,他做了一个后来令自己万分庆幸的事情,那就是给自己的老朋友赫斯打了个电话。
当时,赫斯正好被贝尔实验室裁员了,面临着是进入硅谷的初创公司,还是重回基础科研领域的十字路口。
这对当年的好朋友、好搭档似乎在同一个时刻遇到了中年危机。他们多次相约一起爬山远足,在加州优胜美地等国家公园里徜徉,大自然的美景和造物的宏大让两位科学家感叹自己的渺小,也让他们真正地放空,思考着人生意义和价值所在。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对“受好奇心驱动的科研工作”的热情。白茨格说:“我想做小众的事情,我想走一条并非大家都会选择的道路”。
他也坚信自己的目标是更加清晰地观察细胞里充满生机的生理活动。就是这个初衷驱使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兜兜转转之后,最终回到了自己热爱的科研领域。然而,他需要一个让自己重启科研之路的灵感。
为了拾起荒废近10年的专业,“我甚至相当于重新自学了一遍物理学和光学”,白茨格说。
就在他潜心自学充电的过程中,一篇重要的论文引起了他的关注,也重新点燃了他对高分辨率显微镜技术的热情。
这篇论文是关于一个改变了细胞生物学研究的神奇分子——绿色荧光蛋白(GFP)。下村修最早从水母中分离出这种可以在紫外光照射之下发出绿光的小巧蛋白,Martin Chalfie证明了GFP作为多种生物学现象的发光遗传标记的价值。钱永健的主要贡献在于让人们理解了GFP发出荧光的机制。同时,他拓展出绿色之外的可用于标记的其他颜色的变种,从而使科学家能够对各种蛋白和细胞添加不同的色彩。这一切,令在同一时间跟踪多个不同的生物学过程成为现实。2008年,下村修、Martin Chalfie和钱永健三人因在GFP领域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白茨格开玩笑地说,“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GFP的人,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发现不仅改变了细胞生物学,也将改变生物显微镜技术,因为它开创了巨大的应用空间。”
“我为自己的朋友没拿诺奖感到遗憾”
早在1995年,白茨格就提出了光激活定位显微术(Photoactive Localization Microscopy,PALM)的思路,他的想法是控制荧光分子,每次只让少量几个荧光分子发光,用电荷耦合元件(CCD)记录并拟合每个荧光分子像的中心位置,以时间来换空间,将多次观察得到的位置信息整合起来得到完整的图像。
他的这篇论文“Proposed Method for Molecular Optical Imaging”发表在1995年的《光学通讯杂志》 (Optics Letters) 。那个时候他刚离开贝尔实验室,处于失业状态,然而这篇论文却奠定了他日后获得诺奖的理论基础。但是基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个设想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
随着荧光蛋白“开关”效应的提出,以及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生物学家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等在2002年发明了光敏绿色荧光蛋白,白茨格意识到,他终于找到了可以把自己多年的梦想变成现实的“关键一环”。而这时已经是2005年,他离开科学领域已经有10年的光阴。
时间在流逝,由于担心其他人更早地付诸行动,他和老朋友赫斯这两位失业的“前科学家”决定继续一起合作,快马加鞭把这项技术变成现实。他们来不及申请科研经费,甚至寻找风投资金,于是各自掏出25000美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赫斯家的客厅里,研制出了第一台PALM显微镜,并迅速申请了专利。随后,与光敏绿色荧光蛋白发现者Jennifer Lippincott-Schwartz,George Patterson等NIH科学家合作,利用PALM显微镜清楚地观察到纳米级活体细胞的若干生理现象,这篇以白茨格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在2006年9月的Science杂志。从思路诞生到结果发表,他们只用了六个月时间。这篇论文也成为白茨格获得诺奖的关键工作。
在白茨格重返科研之路八年之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用“震惊”形容自己得知诺奖消息时的心情,同时,他对和自己一起发明PALM的赫斯未能同获诺奖感到深深的遗憾。毕竟,PALM显微镜来自于他们共同的灵感,是他们的共同发明。
他在演讲中多次对赫斯对自己职业生涯中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说道,我毕生的工作都要感谢他。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李明在《超分辨显微,至极至美:201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述评》一文中评价说,“白茨格、赫尔和莫纳将已知的技术推至极限,最早探测到凝聚态体系中的单个荧光分子,利用荧光分子的开关效应,加上物理教科书上的受激辐射原理和数据分析中常用的拟合定位方法,绕开了这个似乎不能突破的极限。他们将光学显微技术带入到纳米尺度,引发了常温下活体生物学研究的又一场革命。他们对科学的追求堪称至极至美。”
回顾科研道路中的关键机遇和转折时,白茨格对年轻科学家和学子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没有什么比你的声誉更重要,职业生涯中总有一些时刻你需要一些前同事和朋友的提携和帮助。你必须要做好你的工作,同时你要诚实地工作,要公平地对待别人,否则真的会有报应。你的声誉是你最重要的资产。”
得益于这些帮助,他获得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珍利亚农场研究园区的邀请,领导该领域的研究。赫斯也随后加入,继续成为他的同事。
这一次,白茨格携夫人吉娜一道回国讲学。他们除了在北大的演讲,还将访问上海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吉娜是安徽蚌埠人,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白茨格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吉娜是一位物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现在从事双光子显微镜技术开发和应用,成果卓著,两人堪称比翼双飞。2014年,白茨格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到中国之后,吉娜的母校蚌埠一中,甚至打出了庆祝标语,称白茨格为“我校女婿”,一时受到中国网友的热议。
在演讲中,白茨格还特地感谢吉娜作为伴侣兼同事,给予自己的支持和帮助,并感激她对自己提出过的中肯的批评。物理学家出身的吉娜认为丈夫虽有物理学博士学位,但在物理方面也不能算天才。她在私下场合开玩笑说,“他认识物理,物理不认识他。”
白茨格在演讲中坦言,自己的获奖技术虽然有用,但已不足以让他感到振奋。他于是继承了2011年因脑癌去世的同事Mats Gustafsson于2000年发明的另外一项技术SIM(结构给光显微技术),并不断加以改进,与其他技术结合,现在可用于活体成像,且实用性更好。他还介绍了自己尚未发表的最新技术——双通道自适应光学栅格光片显微镜(Lattice Light Sheet Microscopy with Two Channel Adaptive Optics)的研究进展。
在他身后的投影屏幕上,演示着一系列用视频呈现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一个画面上可以看到细胞分裂的整个过程,细胞核内的DNA也在荧光蛋白的染色下清晰可见……
当年引领他走上科学之路的,用高分辨率显微镜观察活体细胞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才是比诺奖更让他为之陶醉并欣慰的。
在回答现场一位北大同学的提问时,白茨格说出了自己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不要害怕冒险,不要因为追求安全而搭上别人的便车,要勇敢地开拓属于自己的道路。”
相关新闻
- 2018/03/27
- 2018/03/27
- 2018/03/16
- 2018/03/16
- 2018/03/09
- 2018/03/05
- 2018/03/01
- 2017/02/06